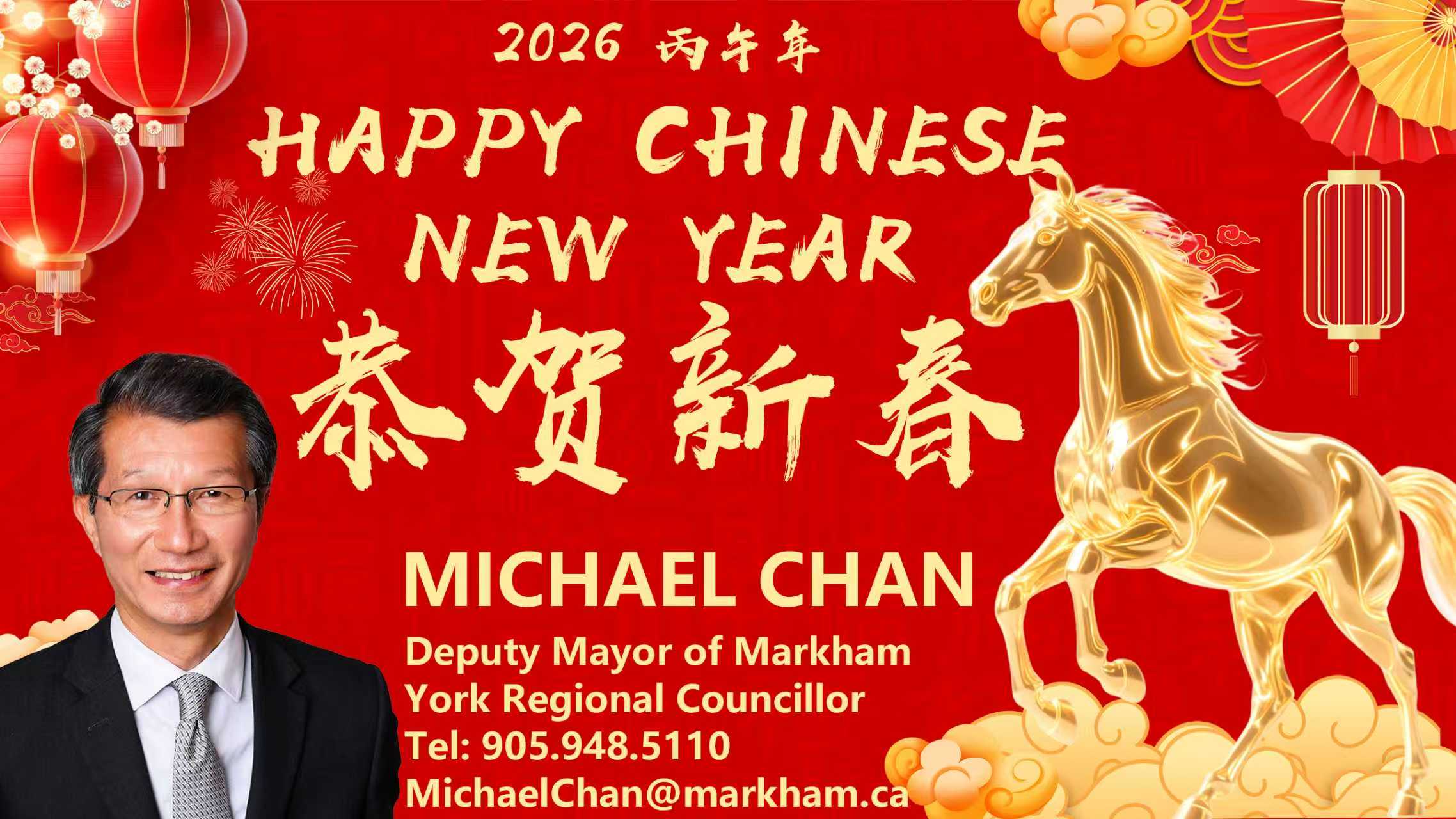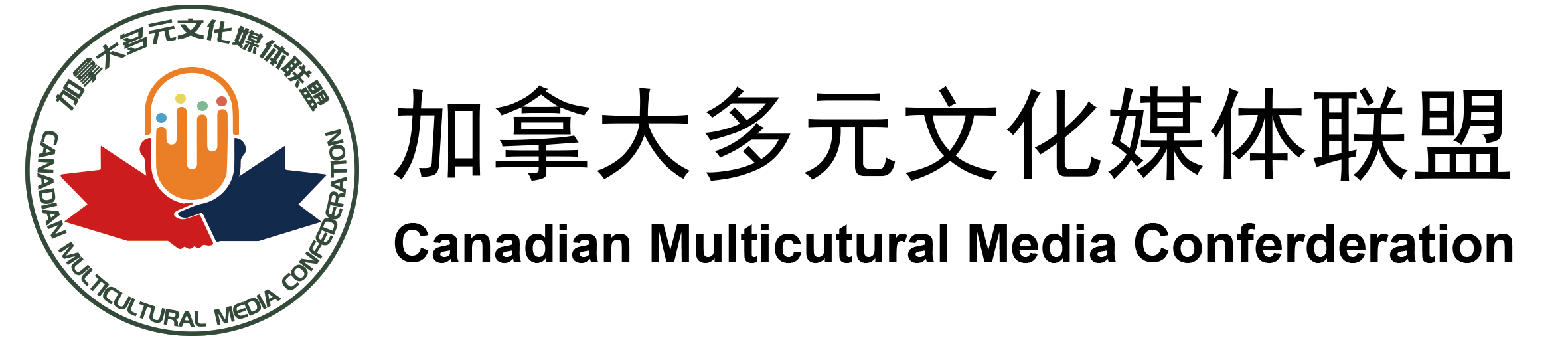【作者:许首秋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有幸受《音乐生活》期刊编辑部的邀请,在青年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李博副教授的引荐下,笔者2025年6月19日赴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对一级指挥、全国政协委员、第76和77届国际青年音乐联盟执委、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四个一批”人才、湖北省人民政府“楚天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武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彭家鹏先生进行了专访。
在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办公室里,这位华发蓬松、颇有小泽征尔之风的著名指挥家以无比亲切温和的语态,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分享其在职业生涯中的宝贵回忆与对指挥这个伟大职业的深刻认知……
1985年彭家鹏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1987年转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学习。1990年通过保研直升硕士研究生,并于1992年获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1996年他以亚洲唯一青年指挥家的身份参加了在荷兰举办的第35届国际康德拉申指挥大师班,翌年入选乌克兰基辅国际指挥大师班,皆以最优成绩毕业。
多年求学期间,他先后受到夏飞云、徐新、郑小瑛、爱德华·杜宁斯、彼得·艾特沃思、古斯塔夫·梅耶尔、曼迪·罗丹等国内外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的悉心指导,在指挥技术和审美观念上获得了双重升华。
在他看来,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指挥教学非常重视技术。国内老师会要求学生精准掌握作品每个声部的“起拍”位置,并且要求指挥能够清晰地给予乐手提示。此外还有节拍、速度、力度方面的控制等等,都要求细腻到位。这种训练模式帮助指挥家们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以至外国导师们普遍觉得亚洲的指挥、演奏乃至其他专业研究者都具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底。而有所不同的是,西方指挥家们多以音乐文化背景叙事下的音乐性表达为核心目标,特别强调在这种审美旨趣下指挥对音色的控制。
由此他回忆道:“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让我们反复练习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Op.68)的执棒,以便让乐曲一开始,定音鼓及低音提琴声部在6/8拍中的连续行进沉稳而准确。同时,他们十分注重谱面细节处的力度控制,告诉我们在某些位置乐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由此,足见我国老一辈指挥家们对乐谱解读与复述的严谨细致。
《雷电波尔卡》
留学期间,老师们则开始和我们讲解勃拉姆斯、贝多芬等人交响曲作品的创作历史背景、情感内涵与立意旨趣,并以此出发教授我们如何控制弦乐组的弓法和管乐组的呼吸。像指挥家曼迪·罗丹,他是拉中提琴出身,就对乐队弦乐的弓法处理特别讲究。他要求我们在每次排练作品之前,必须先为乐队设定弓法及乐句呼吸位置,其设计不必拘泥于谱面的指示表象。就像对贝多芬《bB大调第四交响曲》(Op.60)第二乐章‘柔板’(Adagio)开头处第二小提琴声部‘长—短’节奏的处理,罗丹认为其强弱设计就不能仅仅根据谱面判断,以避免形成“进行曲”的错误理解。相反,他教导我们应考虑到当时贝多芬与特蕾丝小姐的恋情关系,结合“特蕾丝”原文重音后置的发音规则予以阐释,并以轻柔的反复‘默念’表现眷恋与思念之情。”
老师们基于“艺术”表达的精益求精以及对“技术”处理的苛刻追求让彭家鹏受益匪浅、受用至今。也让其充分意识到真正优秀的指挥必须达成“形式与内容”“技术与艺术”的高度融合。而对于“艺术”的追寻旅程也让彭家鹏对“指挥”这个专业有了新的认识。一方面,它不是一个“年轻”的艺术。相比于许多演奏家很早就可以举办独奏音乐会、充分展露个人技术才华来说,指挥这个职业需要更多超越技艺以外的生命经验沉淀,这就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积累和学习,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一个通过不懈努力就可以完全胜任的职位。因为在超越“技术”、奔向“艺术”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不是老师教出来的,也不是自己学(模仿)来的,而是有赖于天赋和顿悟。很多人虽然非常努力刻苦,还是会因为缺少一些“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特质”而止步于此。
尽管作为学生的彭家鹏拥有一条非常顺畅的求学之路,但他的职业生涯开端却不太顺利。1997年,当他从乌克兰回国时,其所在的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却面临着改组的变革,彭家鹏可能面临无团可指的窘境。
这给他带来了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访谈中,他甚至用“天崩地裂”一词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他说道:“毕竟当时我在回国之前刚刚婉拒了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和乌克兰广播交响乐团抛来的橄榄枝,这就相当于直接放弃了进驻欧洲乐团的宝贵机会。这个时期,难过、失望甚至后悔的情绪以及对未来职业生涯的迷茫始终围绕着我。”
就在此时,广播艺术团的领导推荐彭家鹏去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完成赴中国香港和泰国的几场演出。出于对民族音乐作品以及民族乐团指挥模式的好奇,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然而,彭家鹏一去就发现,指挥中国民族音乐作品绝非一件易事。例如在《乱云飞》(京剧《杜鹃山》选段)中,二十件高胡和二十件二胡以及许多打击乐器“自由”演奏,让指挥家顿时手足无措——因为其处理方式与他之前所学习的西方交响乐完全不同。
对此,彭家鹏倒是毫不气馁,甚至还带有一点“不服气”。他不断反问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连西洋音乐都能良好掌控,难道在面对自己国家的音乐时却指挥不好吗?”于是,他暗下决心,拼命自学。通过研究大量民族民间音乐,细致研究彭修文、刘文金、秦鹏章等先生的作品表现技法与意蕴,结合指挥西方交响乐团的既有心得,探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随着与民族乐团的不断磨合,他也逐渐获得了乐手们和音乐界的充分认可,有了更多的指挥机会。1998年,他正式担任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并仅在两年后便率团于维也纳成功举办了音乐会。
这些经历和挑战让彭家鹏很早就清楚地体会到指挥这个职业并非只有旁人所看到的,穿着演出服在台上接受观众们热烈掌声的风光和潇洒。它的背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承受无数艰难困苦与寂寞。
千禧年后,彭家鹏已经作为指挥界的冉冉之星,照耀着国际乐坛。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2000到2012年间,仅在奥地利维也纳一市,他就先后携手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国东方交响乐团、奥地利国家民族歌剧院交响乐团、奥地利国家音乐家交响乐团、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交响乐团、奥地利格拉兹交响乐团、捷克国家交响乐团、吉林省交响乐团、中国红樱束女子打击乐团、中国成都东方茉莉女子国乐团、奥地利雷哈尔交响乐团参演了中国民族音乐会、维也纳中国新春音乐会、庆祝中奥建交四十周年音乐会等重大汇演,成为维也纳指挥台上的中国常客。在奥地利之外,他的指挥足迹还遍布世界各地,包括德国、瑞士、捷克、俄罗斯、美国、日本、朝鲜等。
与此同时,彭家鹏在国内的乐团指导与演出活动同样丰富。其先后担任了中国东方交响乐团;澳门中乐团;中国歌剧院舞剧院交响乐团、歌剧乐团、民族乐团;吉林省交响乐团等团体的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在他的带领下,这些乐团的专业水平不断提升,乐团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十多年间,彭家鹏在中国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形态,还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乐人在民族交响乐创作方面的探索创新引介给西方乐坛。更加宝贵的是,在与西方乐人的交流沟通中,充满民族文化自信的他始终坚定不移并因地制宜地站在宣扬中国审美品位与中华文明精神的第一线。
这里,指挥家向笔者分享了一则故事。
2000年,当彭家鹏第一次携手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龙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之前,其曾与这台音乐会的主持人马塞尔·普拉维先生有过一次关于曲目择取的激烈“交锋”。
他提到:“尽管普拉维先生在1998年就已经开始主持‘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了,但这位老先生还是对中国民族音乐有些误解,总觉得中国民乐都是一些吹拉弹唱的‘小组合’‘小节目’。相比于西方交响乐团而言,中国的民乐应该是‘零散’‘个性’的。所以他就要求我不要演奏民族交响乐,因为他一直认为交响乐是西方的,中国没有交响乐。同时他还建议让我弄些欧洲没有的花花绿绿的服饰、请一些会曲艺杂耍动作的演员过来演出以满足欧洲观众的猎奇心理。”
自然,这种想法和彭家鹏的理念截然不同。在他看来,中国当然有非常优秀的民族交响乐作品,而且这些作品都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曲目库中的“王牌”。这场音乐会就是要把这些优秀的作品与深远的文化传递给欧洲听众。于是,彭家鹏就试图跟普拉维解释,但他仍然固执己见。他还说如果不按照其要求调整,他就拒绝主持这场音乐会。而彭家鹏这边也非常坚持自己的诉求,宁愿不要主持也不愿退步。于是这次合作几乎谈到一拍两散的境地。
彭家鹏继续说道:“在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后,我俩竟然在喝咖啡时不自觉的哼唱中再次寻得同频。在这种共通的音乐语言里,普拉维终于放下了他的执拗与偏见。我就顺势和他介绍起了中国民族交响乐的发展历程,并说服他在听完我们的排练后再行决定是否出任主持。第二天我们在排刘文金、赵咏山创编的民族管弦乐《十面埋伏》时普拉维来听了,大受震撼。老先生甚至激动地摔倒在了地上,把头都磕破了,还去医院缝了针。可他顾不上疼痛,再三和主办方确认晚上的音乐会一定来主持,同时为之前对中国音乐的认识局限而感到抱歉。后来两个多小时的音乐会上,这位老人兴高采烈地为我们前后奔波,让我们都觉得他为人非常坦诚、非常了不起。”
回想起这场两个文明、两段年龄之间的审美碰撞,彭家鹏至今仍会为当时在欧洲乐坛权威面前的冒险举动而心有余悸。可他并没有丝毫后悔,因为他觉得必须这样做。他说:“这既是基于我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自信,也是基于一种责任——当外国人误解我们的民族文化时,我必须站出来予以澄清。”
随着与西方乐人交流的深入,彭家鹏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乐手开始关注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创作,对中国民族乐器特殊音色调配颇为赞赏。他在访谈中提到,这些外国乐手在聆听《春江花月夜》《月儿高》等传统作品时,将琵琶拨弦三两声的轻巧音色比为天籁,乃至一度让他们联想起贝多芬的《“月光”钢琴奏鸣曲》(Op.27之2)。而在面对如郭文景的《御风万里:为管弦乐队与军乐队而作》(Op.27)、唐建平的交响组曲《精卫填海》等中国当代作品时,他们亦沉浸其中。相比于那些过于注重新颖音响效果而缺失感人特质的先锋派实验性音乐作品,他们更喜欢中国音乐中那富有律动变化的节拍节奏和那引人陶醉的旋律递进。
对此,作为指挥的彭家鹏敏锐地意识到,要让西方乐手们在面对中国作品时超越“好听”的表象,进而浸入作品并准确把握内涵意蕴,还需要指挥家的巧妙引导和启发。
以下视频来源于
古典朋友圈
《威廉退尔》序曲
长期的西方交响乐团指挥实践让彭家鹏熟知,西方乐手在演奏如莫扎特的歌剧《魔笛》(K.620)序曲,斯美塔纳《沃尔塔瓦河》(选自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等“本土”作品时,里面处处遵循严格的技艺传承。某个音符用哪个指法、用哪根弦,都是由老师传给学生,再由学生传给下一代学生,百年不变。其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技术维持作品原来的意味与旨趣。这就让许多优秀的乐团在演奏时会不自觉地遵循某些程式,可是这些程式往往又不能直接用于中国作品的演绎。
面对这种中西音乐在技术表现和艺术追求上的双重表达,彭家鹏强调指挥要始终站在乐手的角度,以他们的理解方式进行讲解和排练,从而寻求弥合之道。他认为如果指挥只依照自己心中的思维逻辑就想让乐手们立刻呈现理想的终极效果,是难以做到的。相反,指挥要愿意花费心血与乐手们的心灵不断贴近。大家只有围绕音乐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包括超越人种、族群与文化差异的人类情感共鸣进行讨论,才能深度交融。而这种交流的语言不只是一般语言,更应该是音乐语言。故而,指挥要经常能“说”给乐手们听,同时还要会“唱”给乐手们听。
步入“新时代”,已经跻身国际一流指挥大师队列的彭家鹏再次面对一场重大的挑战:2013年,他在无比繁重的日常工作中仍毅然决定去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跟随著名歌剧指挥家康拉德·莱特纳教授学习欧洲歌剧指挥。
只不过这一次的挑战既不是因为乐团改组,让他不得不去掌握如何指挥中国民族音乐,以谋求职业留存发展的空间;也不是出于民族文明自豪与肩负责任的使命,让他必须向误解中国音乐文化的欧洲权威学者提出证明,而是他不忘初心、渴求极致艺术表达的自我选择。
据彭家鹏所言,他坚持继续深造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对于这所专业院校的向往。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学府,培养了一大批著名指挥家,如祖宾·梅塔、克劳迪奥·阿巴多等。而彭家鹏在十几年间虽一直徘徊于维也纳,却从未进入过这个指挥界的核心阵地进行学习,心中不免存有遗憾。
二是,他觉得自己在歌剧指挥方面还是缺乏一些自信,想通过进修让其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在笔者看来,这当然是出自指挥家的谦逊。众所周知,在乐团指导方面,2003年他就曾与奥地利国家民族歌剧院交响乐团有过合作。2008年,他又担任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的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在演出实践方面,2011、2014年分别在福州、武汉举办的第一、二届“中国歌剧节”上他先后指挥了民族歌剧《原野》、西洋歌剧《茶花女》并荣获大奖。2016年底,他又携手福建省交响乐团、福建省歌舞剧院在福建大剧院完美演绎了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三幕轻歌剧《蝙蝠》(Op.108)。可见,以民族交响乐指挥著称的彭家鹏在歌剧指挥领域也绝非毫无建树。
果不其然,当他历经万难,终于获得破格录取的机会进入学校学习后,导师莱特纳能教予他的,只剩下对比讲解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阿巴多、卡拉扬等指挥家对同一作品的不同处理,及其背后的缘由与效果。
对于为什么要执着于强化“歌剧指挥”这个角色能力的问题,彭家鹏诚恳地表达了内心的想法。他认为,在指挥这个职业中,只有能够完美驾驭歌剧艺术才算达到最高境界。因为歌剧指挥不只是调度乐队,而且要让每个角色、每个场景都珠联璧合。他的这种想法源自小时候受父母在地方歌舞团搞戏曲艺术的影响,以及对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作品的耳濡目染。
所以,他在包括歌剧《汤显祖》在内的诸多排演中,从不只是简单地掌管乐队声音,让其为演唱者作好适宜的铺垫。进一步,他始终把“音乐作业”,即带着钢琴伴奏与主要歌唱演员进行细节校准的核心环节放在首要位置。对于演唱者哪个音要“细”、哪个音要“宽”,彭家鹏都会给出中肯的建议,以便让歌唱家与乐队更好地交融。
除了歌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以外,协奏曲、无伴奏合唱、艺术歌曲等不同形式体裁的音乐作品的指挥也是彭家鹏的拿手好戏,充分显示了其广泛的专业涉猎范围。
在指挥对象上能够做到近乎“全能”,首先得益于其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彭家鹏回想道:“在接受系统专业的指挥学习之前,我就已经有过在沪上不少大学合唱团里担任指挥的经验。伴随着本硕博的分段学习经历,我始终和许多作曲家、演唱家、演奏家们保持密切联系,在大量的演出实践中去接触各类作品。此外,还要不断学习、不断打磨。就如中国的戏曲非常复杂。它的唱腔和西方歌剧完全不一样。无论是高亢粗粝的秦腔,还是字正腔圆的京剧,必须先充分了解它们的艺术底蕴,熟悉其特有的表达手法,才能最为贴切地传达其中的情感。我记得当时排演大型秦腔交响诗画《梦回长安》时就连续半个月和乐团不断排演,非常辛苦。”
其次,是要去研究并且创新指挥法。如戏曲里面锣鼓拍子的掌控就不能拿西方交响乐指挥法生搬硬套。他说道:“像《打虎上山》(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中打击乐‘半拍起拍’这样的特殊方式,就必须不断琢磨并使用自创的方法才能让乐手舒服地加入演奏中。这些关键信息的提示,在指挥的肢体语言或眼神交流中就传递出去了。虽然从观众的视角来看,可能只是关注到我充满激情的外在动作与神态。然而其中皆有章法,这些动作是内在指挥技巧以及音乐情感传递共同驱动的产物,不是简单的肢体动作表演。”
在乐团管理与建设上,彭家鹏同样凸显出了“全能”的指挥能力。他认为,无论是乐团总监还是首席指挥,一定要有独到的艺术策划。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乐团、演出什么样的作品、获得什么样的声音等等,都是彭家鹏经常盘算的问题。
比如关于乐团编制管理和人才引进,他为了吸引顶尖人才进入乐团、优化乐团演出效果,就会向领导层提出各种人事方面的要求。如此,澳门中乐团才能在数年间,通过人员考核、编制扩展、人才引进、多乐团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乐团实力,让其从一个半职业乐团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中乐团,并在国内外各种音乐节上大放光彩。又比如为了让乐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作品演绎体系,彭家鹏一方面充分挖掘乐团已有经典作品曲库,一方面坚持提出让乐团一定要有自己的委约新作。
不仅如此,整个音乐作品从诞生到上演的过程中,彭家鹏还要完成与作曲家、演奏家们的沟通协调,乃至亲自参与到编创与教学工作之中。
彭家鹏向笔者提到:“面对委约作曲家时,我会告诉他们我想要怎样的作品。比如我请作曲家刘长远教授写《第五中国交响乐——光明》时,我就告诉他我要一部如同马勒《#c小调第五交响曲》这样凝聚人类对生命、死亡、爱与希望深刻反思,同时要兼具马勒、韦伯‘柔板’乐章纯粹情感表露的作品。于是作曲家就有了更为明确的创作主旨,最终展现了人们经历病痛折磨、生死离别的外在表象,以及互爱互助、坚信光明的内在精神。
有时候,我对委约创作的要求非常细。曲式结构布局、乐段配器设置、两段连接处理、和声过渡演变、演奏音域选择、作品标题命名等内容我都会和作曲家探讨。在作品创作过程中,我还会要求作曲家发一些小样进行试演。根据实际效果给作曲家反馈,方便其及时修改与调整。我这么做并不是要干涉作曲家的创作,而是想在委约作品中获得适合乐团的声音音色,体现乐团特有的艺术理念与审美追求。
我也会直接参与到一些经典作品的编创工作中。如我曾对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交响组曲《天方夜谭》(Op.35)进行了改编,在保持原有风味的前提下,良好地完成了中西乐器替代或融合使用。”
面对乐团的青年演奏家时,彭家鹏则要求他们完成从“专业音乐学院独奏演奏家”身份向“社会音乐学院乐团演奏家”身份的转换。为此,他总是积极地鼓励乐手们根据乐队需求去重新系统地学习一些原本接触不多的乐器,如中音唢呐、高胡、中胡等。同时他还会引导乐手们转换演奏思维,从原本对高难度民族器乐独奏曲的专注转向对重奏、合奏的重视。这种细节化、“实战化”的乐团延续教育,无疑让青年民乐演奏家们获得了更加丰富的演奏经验。
在彭家鹏如此“全能”的指挥下,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从2017年成立到2019年进行欧洲巡演,从2021年荣获“奥地利音乐剧院·国际交响乐团奖”,再到2023年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短短几年时间,其艺术水准和国际知名度得到了大幅提升。
对于这个成功案例,2021年“奥地利音乐剧院·国际音乐文化成就奖”得主彭家鹏又谦虚地将其归功于理想的乐团起步与良好的地方扶持。他说:“我刚接手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时它是一张白纸,这对指挥来说就是最好的状态,我可以完全依照心目中的中国顶尖职业管弦乐团样貌来绘制建设蓝图。譬如我可以要求乐团编制不能少于85人,以专业淘汰和待遇保障机制维持乐团高水准与稳定性,建立作品委约机制,保证每年新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等等。这种科学的管理机制和欧洲乐团的相关机制较为相似,但又不是完全照搬,我们会根据乐团特色进行设计。在我看来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它既可以很好地保持苏州地方特色,又始终与世界接轨。”
彭家鹏又注意到苏州城市文化对乐团建设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他说:“苏州这座城市历史悠久,也非常与时俱进。苏州人精明干练,同时又充满包容。她能够很快接纳新鲜事物,且爱护人才,苏州政府也对文化艺术十分重视。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总经理与各位领导同样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他们在艺术上不会干扰我的想法。另外,苏州的可贵之处在于这里的人们工作学习都很认真用心。我到这里七八年了,无论是领导、行政人员还是音乐家们,都时刻被这个氛围影响着。这种专心致志不是嘴上说说的,每个人都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亲身感受。”
而笔者以为,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整个集体对指挥有极致艺术渴求的高度认同以及高效同频协作保障。这正如指挥家所说的那样:“很多外人也许不理解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成功,以为只是单纯地有经费支持。经费支持固然是很重要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大家具有共同的艺术理念——我们都是在一种严肃、严谨的艺术追求中经营乐团。自然,有些作品需要契合普通大众的喜好、赢得市场推广,但一些极具专业价值的、受到音乐界认可的优秀作品我们一样极度重视。”
二胡与乐队《二泉映月》
在AI时代的当下与未来,青年指挥家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将同前辈一样,面临更多的困境与挑战。访谈的最后,彭家鹏先生还真挚地为未来指挥家们写下了寄语:
“在选择指挥专业之前,大家一定要清楚指挥这个职业不是只有风光的表面。如果只是追求舞台上的光鲜,那么一开始你的定位就不对。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指挥这个职业是非常辛苦的。这份职业不仅要面对艺术家,更要面对观众、服务人民。它要求你做到‘全面’,即在各类指挥实践中去积累经验。指挥也是非常残酷的职业,有赖于天赋与机遇,还要耐住寂寞。另外,指挥还要懂心理学,要善于与人沟通。怎样调动别人的积极性、怎样既解决问题又不伤害他人,这是一门学问。所以千万不能把自己放置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趾高气扬。其实你和其他人只有所处角度的不同,与其他人一样都只是音乐作品完成过程中的一环。你对他们的关怀和爱应该和你对音乐的爱是一样的。
要记住,一个优秀的指挥就和大厨一样。各种各样的味道如何调配,各有秘诀。然而,这不是拿着乐谱就可以直接上台的。因为作曲家依托想象转化而成的音符毕竟与我们在天天排练实践中所听到的声音有所差别。特别是在民族交响乐作品中,当很多声音配合在一起时,指挥必须有效地控制乐器本身的个性,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指挥也只有在现场反复排演的实践中才能真正体悟其中的真谛。
所以,你要去热爱这个事业,不能有急功近利的心理。如你一直想着‘我一定要成为一个著名的指挥家’,那样多半会失败。青年指挥家们必须要先行沉淀下来、努力付出,才能迎接挑战,并把握住命运赐予的宝贵机遇。”
作者:许首秋 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